题解
《原人论》,唐释宗密撰。宗密,生于公元七八○年(唐德宗建中元年),殁于公元八四一年(唐武宗会昌元年),俗家姓何,果州西充(今四川西充县)人。由于他晚年长期住在陕西终南山草堂寺南圭峰,因此学者又称他为圭峰大师。
宗密出生于富裕家庭,据有关碑、传记载称:「大师本豪盛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。],「家本豪盛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;又说他「家世业儒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。看来他家庭虽然富有,但并非地方豪霸,亦非功勋贵族,而是世代读儒书的平民。正是在这样环境的薰陶下,说到他「髫龀时精通儒学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,或称是「少通儒书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。他写的自叙也说「髫专鲁诰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·本序》。],在给澄观的信中还自称「自髫龀泊弱冠」,「诗书是业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(这里「髫」指儿童的发型,从童年到弱冠,大约是从六、七岁到十六、七岁之间。在这段期间,他是专心熟读儒家经典,可能还准备参加科举考试,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的出路。)
但是密宗在修习儒书的过程中,不满足于只是诵读儒家经传的词句。由于唐朝的科举考试,要求考生背诵经书的条文。如考试方式中有一项为帖经,将经文左右内容掩盖,露出中间一行,再裁纸为贴,即将这一行中用纸随意贴掉几个字,要求考生说出来。这种考试方式,考生除死记硬背外,连经义也不一定理解,更谈不上通经致用了。(另外唐朝的科举制度,考生分生徒和乡贡两类。生徒是在校学生,可以直接参加考试;宗密非在校学生,作为乡贡就要先向当地州、县报名,经考查合格,再举送朝廷。)这种制度,使宗密大为不满,所谓「欲于世以活生灵,负俊才而随计吏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。本来以他的才情,是可以到社会上为民造福,但参加科举考试却要受制于地方「计吏」的推举,因而挫伤了他进入仕途的积极性。
密宗少年时已经是个聪明好学的人,他读书并不专为求得功名富贵,同时对现实的人生也开始进行思考。他曾自称是「好道而不好艺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「道」是对宇宙人生规律性的理解,是最高的智慧;而「艺」则是可供操作的技能,只是一些具体的智识。宗密虽然说过,「纵游艺,而必欲根乎道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他对自己的儒学生涯,一方面承认是「游艺」,即游回在各种技艺之中;另方面亦力图从「道」的理解来指导「艺」。但当时从他的学力来说,对解决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所谓「道」,他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。比如宇宙间万物如何产生?现实人生为什么有贫富贵贱、贤愚善恶、生死寿夭?人之生从何而来,人死后如何归宿?探寻这些问题,儒学中并非完全没有答案,但要在心灵的归属上寻求慰藉,这是入世的儒家难以满足的,只有在宗教方面才有希望得到解决。
正是由于上述原因,宗密在儒学中找不到心灵的归宿,「是则诗书是业,每觉无归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虽然将读诗书作为专门业务,而心中却感到彷徨无计,这就使他对儒学产生怀疑。所以他虽在「髫龀时精通儒学」,但到「弱冠」成年后,却开始「听习经论,止荤茹,亲禅德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。即对佛教有所接触。他既去听佛经的宣讲,同时遵从佛教素食的生活方式,并对佛教教义作理论研究。他接触佛教也是从浅入深,初时对因果报应论比较欣赏,「决知业缘之报,如影响应乎形声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这段期间据宗密自述:「余先于大、小乘法相教中,发心学习数年。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他这里涉及到讲业报的人天教及小乘、大乘法相教等教义。但由于缺乏名师指点,故仍未解决心中的疑难,所谓「无量疑情,求决不得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,因而「惑情宛在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后来宗密说到这个时期学习儒、佛两家教义的情况,是「俱溺荃蹄,唯味糟粕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·本序》。],只懂得一些粗浅的皮毛,因而不免感到失望。
宗密成年后初步学佛,感到收获不大,于是又想转归儒学。为了能直接从学校赴考,他就到遂州(今四川遂宁县)义学院学习,「将赴贡举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,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,这一年他是二十三岁。据宗密自叙,谓:「二十三又却全功,专于儒学,乃至二十五岁过禅门。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这里讲「过禅门」,指从道圆禅师出家,但时间与两篇传记有出入。据《宗密传》称:「元和二年,偶谒道圆禅师,圆未与语,密欣然而慕之,乃从其削染受教。」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则称:「宪宗元和二年,将赴贡举,偶值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法席,问法契心,如针芥相投,遂求披剃,时年二十七也。」两处记载年份相同,但推算年龄,既非二十五、也非二十七,而应该是二十八岁。
不过年岁记载虽是有些出入,而宗密随道圆出家事却几处所述相同。当时他正在遂州义学院读书,准备应考,适逢道圆禅师到遂州开设道场,宣讲佛法。宗密当时思想正在游移不定,得到消息后就去参加听讲。因这次见道圆是偶然机会,所以两传说是「偶值」、「偶谒」。可能他听讲时提出问题,而道圆却「未与语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,没有给以回答。但道圆虽没有说话,而宗密却感到这位禅师气度非凡,「俨然若思而无念,朗然若照而无觉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。],清朗、深沉而又安详。无言的智慧在启发后辈的思考。宗密此时却突然进入悟道的境界,「问法契心,如针芥相投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,也就是禅宗以心传心所取得的效果。由是宗密决定放弃儒学科举之路,「落发披缁」,即跟从道圆出家,这是他人生际遇的一大转折。
至于道圆所属宗派,宗密认为是禅宗南派惠能的传人,其世系为:曹溪惠能——荷泽神会——磁州智如——益州南印——遂州道圆,由是宗密自居为荷泽宗神会的四传弟子。
宗密随同道圆之后,从儒学正式归依佛门,寻求人生安身立命之道。他禅悟功夫虽有长进,但感到问题并未完全解决,如身(肉身)与心(精神)的关系,色(物质现象)与空(抽象本体)的关系,以何者为本?似还存有疑难。他在参见道圆时虽多次询问,道圆仍是一贯作风,并不具体回答,却给宗密一部《华严法界观门》,任他自己参悟。
宗密得到《华严法界观门》,开始潜心研究。这部华严宗早期论著,相传为道顺(公元五五七——六四O年)所作,讨论色空、理事关系。全书分三部份,第一真空观,讲色空关系。第二理事无碍观,讲理事圆融关系。第三周遍含容观,讲事事无碍关系。宗密从书中初步领会各种对立矛盾的融合问题:如净刹与秽土的融合,诸佛与众生的融合,时间上则有三世的融合,空间方面有十方的融合等等。这是为宗密思想走向华严宗的先导。
宗密融合思想体系的完成,还得力于《圆觉经》的启示。据说他在道圆门下当「沙弥」时,「一日随众僧齐于府吏任灌家」,「得《圆觉》十二章,读一、二章,豁然大悟,身心喜跃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。宗密为什么喜欢《圆觉经》?这部经的基本内容,承认众生皆有「圆觉」,即自身具有圆满无缺的觉性。这种觉性是至净纯善,自性具足的「真心」,只是由于世人受尘俗所秽染
,各种贪瞋杂念使觉性迷失,因而陷入生死轮回。如能通过自身的悟性修持,排除尘世各种贪瞋爱欲的秽染,觉性就可以得到恢复,即承识众生可以成佛。
宗密经过对《华严法界观门》和《圆觉经》的研修,对原来人世间的死生寿夭、贫富贵贱,以致身心、色空关系等问题,都有所理解。但对佛教不同宗派各据经论所出现的岐异和矛盾,觉得仍有疑难。「至于诸门差别,心境本末」,他感到「犹未通决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。由于他读《圆觉经》后,将悟道心得告知道圆,道圆认为他应当「大弘圆顿之教」,主张他外出游学以增广学识,于是宗密就带着疑难去寻求答案。
宪宗元和五年(公元八一O年),宗密来到湖北襄阳,在恢觉寺见灵峰和尚。灵峰是华严四祖澄观门下,得知宗密的学问和追寻的疑难问题,在重病的情况下,将「经及疏钞」授予宗密。据宗密所记,谓「攻华严大部,清凉广疏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。这指的是《华严经》,清凉国师澄观写的《华严经疏》和《华严大疏钞》。宗密得到华严大法十分高兴,说到他自己「吾辈遇南宗,教逢《圆觉》」,「今复得此大法,吾其大幸矣!」[注释:语出《道圆禅师法嗣》。]
宗密得到华严大法,自认为解决了他一生的疑难问题,使他的心境豁然开朗,自称谓「一生余疑,荡如瑕翳,曾所习养,于此大通,外境内心,豁然无隔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据此对佛教内部各宗派之分,他认为应该用圆融无碍思想来加以包容。而对某些宗派,包括禅宗的缺陷,则说「所恨不知何会」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,由此宗密产生归宗华严的思想。到元和六年(公元八一一年),宗密回到东都洛阳,据说曾拜谒神会墓塔,可能有与先师作别之意。但宗密并未抛弃禅宗,而是纳入华严圆融在一起,这是形成宗密思想的特色。《原人论》可以说是圆融思想的产物。
宗密归宗华严的经过,他在元和六年九月十三日,给澄观写了一封信[注释:语出《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》。]。信中详述自身的学业经历,及修习华严的心得体会,并表述要求归向华严的意愿。澄观十月十二日回信,对宗密的见解给予肯定,称「得旨系表,意犹吾心」[注释:语出《清凉国师诲答》。],同意收纳为门徒,并称誉为「转轮真子」。意思是说,宗密将成为能推转佛教*轮的可靠人选。宗密接到澄观回书后,十月十三日再写信给澄观,表达感戴之情。到年底宗密亲到长安拜澄观为师,澄观对他十分赏识,声称「毗庐华严能随我游者,其唯汝乎!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,可见对宗密寄以厚望,从而奠定他后来作为澄观继承人的地位。
宗密归入澄观门下,先是执弟子礼随侍左右,后来名声逐渐增大,从元和八年(公元八一三年)开始,受各寺庙邀请,外出进行讲学交流,并且有机会到各寺「遍阅藏经」[注释:语出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。],因而学问更加长进。他一面继续研究《圆觉经》,同时与其他经论的思想进行比较。大概在元和十年到十一年之间,为避开都市的烦扰,他进入终南山智矩寺开始撰述,写成《圆觉经纂要》等两部书稿,并继续读寺中藏经。三年后(元和十四年)下山到长安,在兴福寺、保寿寺继续写作。长庆元年(公元八二一年)又回到终南山,先后在草堂寺、丰德寺等地居住,在此期间著述不绝,完成他的大部份著作。
由于他在佛学上的成就,引起朝廷的关注,太和二年(公元八二八年)庆成节那天,唐文宗诏见宗密,「问诸法要」,询问关于佛法要义,并赐给他一件紫色袈裟,又赐号「大德」,表示他在佛教中的崇高地位,由是「朝臣士庶,咸皆归仰」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,受到官民各界羣众的崇拜。
宗密在京师逗留三年后,太和四年他上表请求归山,并继续从事著述。到武宗会昌元年(公元八四一年)正月六日,「坐灭于兴福塔院,俨若平日,容貌益悦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,保持高僧坐化的形像。当时他俗龄六十二岁,按出家算的僧龄达三十四年,遗嘱不留尸骨,不立墓塔,也无须悲悼,表明人去我空之意。后经过唐武宗灭佛的所谓会昌法难,到宣宗时再兴佛教,追谥宗密为「定慧」禅师,立墓塔名「青莲」,「持服执弟子礼,四众数千百人矣」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。可见宗密身后在群众中仍有深远影响,并被推为华严五祖。
宗密的著作,据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记载:元和十一年春,在终南山智炬寺出《圆觉科文》、《纂要》二卷。十四年于兴福寺出《金刚纂要疏》一卷,《钞》一卷。十五年春,于上都兴福、保寿二寺,集《唯识疏》二卷。长庆元年,退居鄠县草堂寺。二年春,重治《圆觉经解》。又于南山丰德寺制《华严纶贯》五卷。三年夏,于丰德寺纂《四分律疏》三卷。至冬初,《圆觉》著述功就,《大疏》三卷,《大钞》十三卷。随后又注《略疏》两卷,《小钞》六卷,《道场修证仪》十八卷。前后著《涅槃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兰盆》、《行愿》、《法界观》等经论疏钞,并集诸宗禅言为,《禅源诸诠集》,及酬答书偈议论等,总九十馀卷[注释:语出《五祖圭峰大师传》。]。
另据《宗密传》载:乃著《圆觉》、《华严》、及《涅槃》、《金刚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唯识》、《盂兰盆》、《法界观》、《行愿》等疏钞,及《法义类例》、《礼忏修证图传纂略》,又集诸宗禅语为禅藏,总而序之,普酬答书偈议论等。又《四分律疏》五卷,《钞悬谈》二卷,凡二百许卷[注释:语出《宋高僧传·宗密传》。]。
对两传宗密著述数量的不同,可能他所编纂的《禅源诸诠集》一百卷,《圭峰大师传承》未有计算在内。就按两传所列不完全统计,宗密的著作量是相当丰富的。至于现存的重要著述,近人汤用彤曾列记如下:
《金刚经疏论纂要》二卷
《华严经行愿品别行疏钞》六卷
《注华严法界观门》一卷
《圆觉经大疏》十二卷
《圆觉经大疏释义钞》十三卷
《圆觉经略疏》四卷
《盂兰盆经疏》二卷
《华严原人论》一卷
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四卷,即《禅藏》序
《禅门师资承袭图》一卷。以上均存[注释:语出汤用彤:《隋唐佛教史稿》。]。
这里所列的《华严原人论》,上述宗密的两传均无记载。由于此书内容与《大疏》、《大钞》有相似的地方,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:《原人论》与《大疏》撰述的先后,在目前研究的情况下,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[注释:语出鎌田茂雄:《儒道的气与佛教——宗密的气》。]。
另据董群的意见,认为与宗密同时的韩愈(公元七六八——八二四年),在长庆四年(公元八二四年)写过一篇<原人>,而宗密的《大疏》则作于长庆二年(公元八二二年)。从内容看,《原人论》却针对韩愈等人的儒学及其渊源,也针对道家道教,兼及佛门权浅之教,即对各宗派关于原人学说作一全面评判,故其撰述时间,可能是在韩愈<原人>篇之后,在《大疏》的基础上写成[注释:语出董群:《唐代佛教学者宗密融会三教思想的分析研究》。]。
从上述宗密一生学养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,我认为《原人论》是他归山后的晚期著作,也可以说是他思想比较成熟时所写。宗密一生,从「少通儒书」,到学法禅门南宗,再归化华严,成为有道高僧。他智识广博,思辩敏锐,且善于融合诸家之长,为己所用。从《原人论》的内容看,正是符合他后期的思想特点。
宗密的,《原人论》,前有小序,后分四节。序言部分,认为人为万物之灵,但宇宙间万物以至人类生命如何生成,若要极本穷源,儒、道两家及佛教一些低层次的宗派都是不能解决。于是他袭用判教的形式,既依次对各宗进行评判,而最后则吸纳各家,将三教融合于一乘显性教,以会通本末作结。全文反映出宗密后期思想的包容性。
《原人论》第一节为<斥迷执>,这是针对习儒、道者的批评。他指出儒、道二教认为「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」,那么人们就无法去避祸求福,只有听天由命。但世上却是「贫多富少」、「贱多贵少,乃至祸多福少」,如果多少都是由天定,天何以不公平呢?对「无德而富,有德而贫」的现象又如何解释?如果说「皆是自然生化」,并无因果关系,然则「太平」治国,可以不倚靠「贤良」,能成为「仁义」之人也无需接受教化。而且天地之气本属「无知」,人禀「无知之气」,何以会变得「有知」;同样草木「亦皆禀气」,何以就「不知」呢?宗密提出这些质询,就是对儒家天命观和道家元气自然论的评判。据此宗密将儒、道说成是思想迷误的外教。
《原人论》第二节为<斥偏浅>。宗密认为佛教中各宗派,有由浅到深的不同层次,可以分为五等:一、人天教,二、小乘教,三、大乘法相教;四、大乘破相教,五、一乘显性教。这一节所讲的前面四个宗派,他认为都有偏失和不足的地方,所以称之为「偏浅」并逐个提出评判。
一、人天教。宗密认为这只是对初入门的佛教徒讲最简单的因果报应的道理。如说行善事死后升天堂,作恶的人死后入地狱,成为饿鬼、畜生。这种教义讲报应虽然不错,但「谁人造业,谁人受报?」即是说一个人今生犯罪或行善,死后由谁接受报应?如果说报应在来生,那么「修福」的人会感到委屈,而「造罪」的人却占了便宜,那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呢?据此宗密认为人天教「虽信业缘,不达身本」,在相信佛教所讲业报因缘时,没有讲清楚人生的本源关系。
二、小乘教。这种教义将人的身心说成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元素相互和合而成,即认为自己的身心为一常住不变的实体,不能了解此身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存在,不过是因色、心的不同元素假合而成的一种幻相。而小乘教却把色、心二法合贪、瞋、痴三毒作为一切生命存在的根本,那么色、心自体就应该永无间断,但在无色界天,没有构成色法的四大元素的存在,又安能维持此身而不断绝呢?可见修习此教的人,并没有弄清楚此身存在的根本。
三、大乘法相教。此教义认为一切有情的存在,自然而有八种识,其中阿赖耶识,是一切存在的根本。由阿赖耶识变现出能产生各种意识的识根,衍生出第七末那识,又各自分出所缘的境界之相。这些所缘境界之相,既然是由识所变现出来,所以都是没有自性的虚幻假相,但由于无明妄想覆盖的缘故,才产生一种错误的执见,以为是真实的存在,并由此而造就出各种因素。宗密提醒人要悟出这种道理,「方知我身为识所变,识为身本」。
四、大乘破相教。此宗教义是要破除大小乘包括法相宗的执著,显示真如佛性本来空寂的的大乘教理。此宗质徇法相教「所变之境既妄,能变之识岂真?」所以认为各种意识,无非是各种因缘假合而成,都是没有自信的幻相。「是知心境皆空,方是大乘实理」。宗密对破相宗虽然有所肯定,但觉得仍有不足之处。他指出如果「心境皆无」,「都无实法,依可现诸虚妄?」即如虚妄的梦境,还是依存于「睡眠之人」,「今既心境皆空,未审依何妄现?」所以宗密批评此种教义只是破除各种执著之心,并没有明确表述真如佛性的本义。
依上所述,宗密认为这四种教义,都有其不足。如果修习这些教理,知道并不完全解决问题,故可以名之为「浅教」;如果将各种教义的执着认为能解决问题,这种认识只能说是一种「偏见」,所以从修习的人而言,上述四种可总称为偏浅之教。
《原人论》第三节为<直显真源>,即最真实了解佛教教义的宗教,宗密称之为一乘显性教。他认为上述各宗理论上都有片面性的缺点,只有「一乘显性教」(华严宗)才能显示最高、最圆满的真理。
宗密所宣扬的大乘显性教,认为一切有情之物,本来都有灵明觉知之性,众生由于不能了解这一点,觉性为无明妄想所蒙蔽,才造成种种因业,受生死轮回的痛苦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指出:「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」,只是由于「妄想执著」而不能证见。因此宗密现身说法,告知一切有情众生,本来是具有无上佛智,所以必须以佛的行为来规范自己,使人心与佛心相契合,这样就能寻回迷失的觉性,进入圆通无碍的妙境。他要众生了解,只要能息妄归真,认识到真心才是衍生一切的根源,只有做到这个地步,才算得是掌握住能穷究人生一切存在的真谛。
《原人论》第四节为<会通本末>。宗密在前三节中,用判教形式,将儒、道外教及佛教中的大、小乘等宗派,一一加以批评,最终归结到一乘显性教为最高真理。但他并不是完全否定其他教派,而是在评判其缺点后,用一乘显性教加以包容,所以说「会前所斥,同归一源,皆为正义」。这是他写作《原人论》的本旨,也是他后期思想成熟的表现。
宗密对教内外各宗派,既是「节节斥之」;在评判后根据不同层次,逐步做「本末会通」工作。他首先阐述一乘显性教的基本教义,承认人生的本源是「唯一真灵性」,这种最初存在的真灵之性,是「不生不灭,不增不减,不变不易」的真心。由于众生对此「不自觉知」,故真心被「隐覆」而不能显现,称之为「如来藏」,有「生灭心相」的能力,而大乘破相教却要「破此已生灭诸相」,因此破相教一方面受到宗密的批评,同时表明破相教实为一乘显性教所包容和会通。
对大乘法相教认为阿赖耶识是最初存在的本源。从宗密看来,阿赖耶识只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与如来藏「生灭妄想」相结合的产物,所以「此识有觉、不觉二义」。如果是觉识,就不会去发动生起外境;如果是不觉,那么阿赖耶识就会起心动念,宗密指出是「依不觉故,最初动念,名为业相」。正是由于没有觉悟,因而起动出本是空无的妄念,并对此妄念加以执著。这就使阿赖耶识「转成能见之识,及所见境界相现」,即变现出外境和人自身。据此宗密认为:法相教的阿赖耶识,也是由一乘显性教会通而来,只是由于对真心觉悟不够,才使如来藏出现「生灭心相」的缘故。
对小乘教的会通,是沿着大乘法相教阿赖耶识的变现而来。阿赖耶识生起外境,而众生「又不觉此境从自心妄现,执为定有,名为法执」。小乘教义就是将外境中种种事物,没有觉悟到是自心妄念所现,而执着为有,称之为法执。由于这种执著,产生了外部存在与我自身的不同,所谓「遂见自他之殊,便成我执」。小乘教主张,空法我有,以身与心识为人的的本源,从一乘显性教的会通本末来说,小乘教比法相教更低一个层次。
小乘教之下为人天教。人天教以业为人生之源。由于「执我相故,贪爱顺情诸境,欲以润我;瞋嫌违情诸境,恐相损恼」。这种对我的执著,当我处顺境时就产生贪爱,处逆境时就觉得瞋嫌,加上「愚痴之情,辗转增长」,由此促使人们造作种种善恶之业,并受到相应的果报,造恶业的转生于地狱,或成为饿鬼、畜生;造善业的则转生人道。一乘显性教对人天教,是在比小乘教又再低一个层次上会通。
最后是会通儒、道。宗密既批评儒、道的迷执、又是以本教会通末教,承认儒、道思想的合理性,以达到三教圆融。儒、道以元气、自然、天命、大道为人源,宗密对此逐一加以剖析。
宗密缘著人天教造业的思路,众生如能造善业,「心神乘此善业,运于中阴,入母胎中,禀受气质」到「十月满足,生来名人」。这是承认由于禀受父母气质,经过十月怀胎而成人,这就融合了以气为人之源的儒、道气化论思想。
宗密还从业报论出发「谓前生敬慢为因,今感贵贱之果」。所以或有出现「无恶自祸,无善自福,不仁而寿,不杀而夭」等现象,都是由于「前生满业已定,故今世不同所作」,这种因果报应是「自然而然」,即必然会自然发生的。他认为儒、道那些外学的人,由于「不知前世」,只看到眼前而讲是一种「自然」,那就无法解释受报的原因。只有承认业报论这个前提,儒、道的自然论是可以接受和会通的。
同样从业报论出发,宗密认为有的人少年时修善,老年时反而造恶,也有少时造恶而老年修善的,所以到今世有的人「少小富贵而乐,老大贫贱而苦,或少贫苦老富贵」。外教学者不知这是业报,而认为是「由于时运」,亦即是归结为天命。宗密认为如承认因果报应这个前提,天命论也可在融合之列。
最后对儒、道的大道生成论,宗密用阿赖耶识的变现原理来加以会通。他承认有「混一之元气」与「真一之灵心」,但认为「元气亦从心之所变」,「是阿赖耶相分所摄」,据此,「则心识所变之境乃成二分,一分即与心识和合成人,一分不与心识和合,即是天地山河国邑」。这就将儒、道所讲的自然大道,成为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见分与相分之境,而「元气」对于「心」则是处在从属地位。
《原人论》写到这里,从本至末,节节会通,而是以本统末,即是以一乘显性教为本,以此会通佛门其他各宗并及儒、道外教,最后达到三教圆融的境界,这就是宗密撰写《原人论》的本旨。
《原人论》又称《华严原人论》,是属于华严宗的经典。宗密本人,后又被尊为华严宗五祖。但从本文上述,宗密对人生哲理的认识和体验,即经历过相当复杂的进程。他从少通儒书,到投身禅宗南宗门下,最后归宗华严,不断对诸家教义进行探索,以寻求人性的本源及其安身立命之道。由于宗密修习诸家教义时,不是简单弃旧图新,而是经过扬弃吸取诸家之长再综合创新。《原人论》既是他晚年成熟的作品,并不是单纯阐述华严教义,从会通本末到三教圆融,在佛教典藉中是占有特殊地位。
《原人论》会通三教的思想,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哲理化,起到重大影响,对促进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,《原人论》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(本书以金陵刻经处印同治十三年鸡圆刻经处本为底本,并参校频伽精舍《大藏经》本。为了阅读方便,除依原来分章外,又以文义为之分段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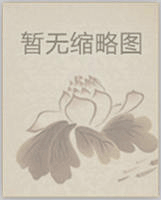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题解 《原人论》,唐释宗密撰。宗密,生于公元七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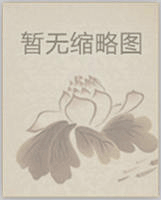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4直接显示一切存在的真源——指了知佛教教义的实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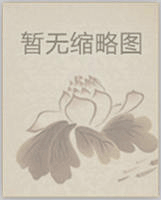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编序 敲门处处有人应 《中国佛教经典宝藏》是佛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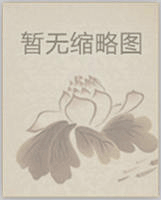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附录(一) 华严原人论解卷上(长安大开元寺讲经论沙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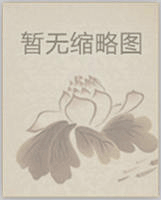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附录(二) 若皆是我,则成八我, 二细析二,初析色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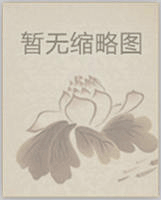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源流 宗密撰写《原人论》,归结到会通三教的圆融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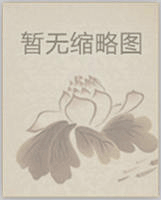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2斥责迷惑的固执——指学习儒、道的人 译文 儒、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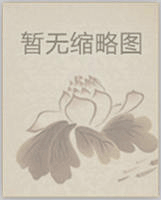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3斥责偏浅的教义——指修习佛学而不了解教义的人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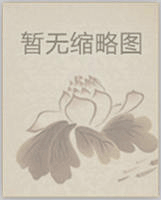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解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,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,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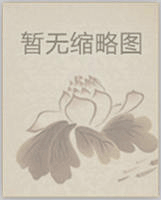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经典 1序 译文 一切有情生灵生生不息,都有其存在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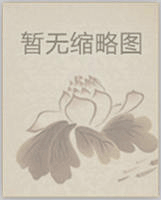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源流 宗密撰写《原人论》,归结到会通三教的圆融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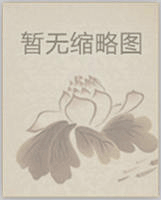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解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,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,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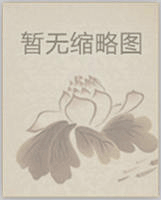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经典 1序 译文 一切有情生灵生生不息,都有其存在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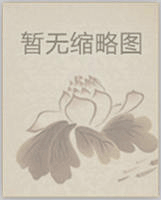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2斥责迷惑的固执——指学习儒、道的人 译文 儒、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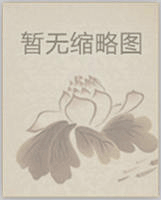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3斥责偏浅的教义——指修习佛学而不了解教义的人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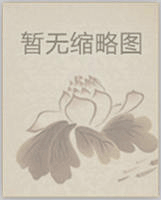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4直接显示一切存在的真源——指了知佛教教义的实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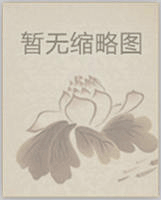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5会通本末各教 译文 真如法性虽然为一切存在的根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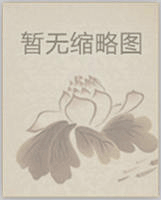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附录(一) 华严原人论解卷上(长安大开元寺讲经论沙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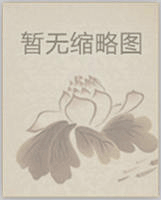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附录(二) 若皆是我,则成八我, 二细析二,初析色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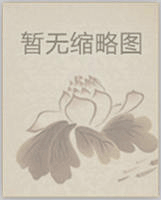
华严原人论 李锦全 释 总序 自读首楞严,从此不尝...